|
<见证北大文革>——名师回忆录 怀念周一良先生 作者: 马洪路 [作者授权独家首发,版权所有,转载须知会] 1964年秋,当我从东北的沈阳市来到北京,来到仰慕已久的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的时候,有幸见到了许多著名的历史学者和考古学家,包括翦伯赞、向达、周一良、苏秉琦、宿白、张芝联、邓广铭等,以及一批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中年学者田余庆、张传玺、邹衡、严文明、俞伟超、孙淼等。其中,给我印象最深、使我受益最多的,无过于周一良先生。 我入学的时候,正逢“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主席心底运筹的时候。后来知道,当时“四清”运动由于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而难以开展下去,教育、卫生和文学艺术领域的许多问题让毛泽东夜不能寐,毛泽东对文学艺术和学术有了多个严厉的内部批示,准备大动干戈。
山雨欲来风满楼,当时的北大,已经闻得到暴风雨到来之前空气中的水腥味儿了。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走进燕园,走到未名湖畔的。 入学不久,我们上的“世界史”第一堂课,就是周一良先生讲授的。面对新生,先生当时讲的内容无非是这门课程如何重要和怎样才能学好,但先生在黑板上大书的5个“W”却令我们永远不能忘怀。他用“Who、Want、Way、When、Where”5个单词风趣而系统地阐述了学习的意义、目标、方法和技巧,使我从内心叹服:“北大就是北大!”
后来了解到,一良先生祖籍安徽至德,出身于一个显赫的世家。他的曾祖父周馥(1837——1921),字玉山,别字兰溪,室名师古堂,官至两广总督,《清史稿》中有传。周馥一生著述颇丰,有《周慎公全集》刊行于世,其中《治水要术》十卷,是最为专门之学术要著。
周馥有六子三女。一良先生的祖父学海,为长子。周学海第三子明杨,后改名暹,字叔弢,以字行,晚年号弢翁,乃周一良先生之父。周叔弢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民族实业家,第一流的古籍和文物收藏家。解放后曾任天津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一生收藏文物、图书极为丰富,后将所藏宋、元、明、清刻本、抄本和校本,以及其它中外图书5600多种,近37000册,悉数捐献给国家,分别收藏于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天津市图书馆等;还捐献文物1260多件,藏于天津艺术博物馆。
周一良先生是周叔弢的长子,字太初,1913年生于青岛,1920年在天津入私塾读书,1930年入北平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科,1932年转入历史系学习,开始发表历史研究文章,显露出扎实的学风与日益深厚的功底。先生毕业后受知于国学大师陈寅恪,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1939年秋赴美国哈佛大学深造,1944年获博士学位。抗战胜利后,归国任燕京大学国文系副教授,1946年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从此成为北大的历史学科带头人之一。
1965年,一向用兵如神、气吞山河的毛泽东开始了发动文革的各种史无前例的舆论准备,北大的文、史、哲各系陆续对过去传统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教材改革展开了学术讨论,并从教育扩展到几乎整个文化领域。我们的学习,当然也面临着改革的尝试。
按理说,我在历史系的考古专业学习,与执教世界历史的一良先生是不会有过多交往的。但是先生的学识与情操吸引着我向他靠拢,或者我的求知渴望和认真也引起了先生的注意,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两年比较正常的学习生活中,我有幸当面向先生请教过一些问题,总是能得到他的谆谆教诲。 当“文化大革命”彻底打乱了一切秩序的时期,由于反对聂元梓的共识,我和先生则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并结成了忘年交。这使我在离开燕园之后,孤身来到辽北荒僻的小村庄当中学教师时,还不时收到先生从北大燕东园他那居住多年的灰色小楼里寄给我的书信,鼓励我克服困难,正视人生,为国家作出应有的贡献。他在《世界通史》重新出版后,亲自签名邮寄给我一套,甚至当他东渡日本访问时,还特地把一桢在日本青森县的印制精美的菜单寄给我以做纪念。
最使先生和我都难以忘怀的,并最终奠定了我们师生之谊基础的,是1967年先生被从“牛棚”解放出来之后的一次相遇。记得是7月7日的晚上,我正在“大饭厅”前面西侧的一处大字报棚看大字报,突然落下的一场大雨把我逼到30楼的门洞下躲避,恰好路过的周一良先生和他的夫人也到这里暂时避雨。他向我详细问询了1966年10月发起和组建“井冈山红卫兵”的来龙去脉和因此挨整的一些情况,对我们敢于反对聂元梓的勇气表示公开的同情和赞许,也明确表示了对聂元梓倒行逆施的愤慨。
那场雨下得时间不短,我们得以第一次有较多的“非学术”的情感交流,从此便加强了联系。1972年5月19日先生给我的信中,还认真提起这件事。后来我几次去先生家里看望他时,他也常常谈起这件事。 在“文革”中,一良先生所遭受的迫害是很惨重的,但他很少在公开场合提及。据和他一起被关押在北大最早发明的“牛棚”里的郝斌先生回忆,可知先生所受迫害之一斑: 我们被关的地方叫太平庄。在明十三陵的定陵北边,相距五、六公里。这里原是昌平县绿化大队的一个林场,砖房二、三十间,坡地八、九块,分布在几个山头上。
大队“牛鬼蛇神”到来之前,已经形成监管规矩。一日三餐,餐前在毛主席像前列队,弯腰低头,背诵“语录”,而后齐声一喊:“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接着,一个一个分别喊出自己的名字,但在姓名之前,要加上自己的“帽子”。
每次听到集合哨响,要跑步列队,迟到的不能入列,那就是一顿老拳了。集合的操场在山坡中间,路面高低不平。我是腿脚利索的,跑到位置,迅速摘下眼镜,放在手里,听到一声“解散”,才敢戴上——挨两个嘴巴,还受得了,眼镜如果打坏,行动由此迟钝,走路、干活儿处处有错,那就天天有打了。周一良先生的眼镜被打坏,幸亏他有一副备用的。高望之的眼镜被打坏,看着都让人担心,不知道碎碴儿会不会掉进眼里,可是不戴又怎么办呢…… 周一良先生的学术造诣是有口皆碑的,他的一生却几经跌宕,是政治在捉弄他的命运。 对于周一良先生,历史系的周南京教授后来回忆了这样一段往事:
“我还想起了历史系一个令人难忘的人物——文革期间令历史系教师闻风丧胆的炮兵战斗队的光杆司令。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文革初期有一天在三院院内,‘炮兵司令’向排列整齐的历史系的‘黑帮’和‘反动权威’们训话。也不知他哪根神经突然受到刺激,脸色顿时铁青,眼珠灯笼般地突出,大吼一声,给周一良教授重重地一记耳光。我正好路过,看到此情景,不觉心灵震颤,惊谔不止。因为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目睹学生打自己的老师,而且是北大的知名教授。”
这是燕园里上演的何等残酷的悲剧! 1952年入北大历史系的陈小川先生这样回忆周一良先生:
“周一良先生是唐史专家,有极深的造诣,给我们讲亚洲史。我与周先生接触较多,因为周先生是我毕业论文的导师,每周都需要定期向周先生汇报论文的写作情况。我的论文题目是《甘地及其学说》。周先生对我的指导是耐心负责的。周先生第一步就是让我带信去见时任东语系主任季羡林先生,信的大意是同意我在该系阅览室借阅图书。我记得信中有一句‘予以惠便’之言,可见周先生的热情负责。”陈小川还深情地回忆了周先生对治学中的卡片积累、资料收集、文章结构和章法、乃至内容取舍都对学生进行细致的辅导。他回忆到:“使我感动的还有他的谦虚谨慎、平易近人。我每次去见周先生,他都是让我先坐下再谈。有错误的地方,他也不直接批评,只是说:那样写更好一些。周先生不仅在做学问上,而且在做人方面,也深深地感染着我。厚德载物,这种高尚人格、大家风范,我们的老师都具有的这种素质与修养,使我们敬佩,是我们的榜样。” 经历过文革十年的磨难,吸取了“梁效”的教训,先生以古稀之年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焕发青春,发表了大量重要著作,包括对《三国志》、《晋书》、《宋书》、《洛阳伽蓝记》、《世说新语》等的研究,其中对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研究在学术界影响极大。他于1989年开始撰写的自传《毕竟是书生》,对自己的学术生涯作出了恰当的评价。1993年初,先生的八十岁生日《纪念论文集》出版。我在这年深秋到先生家中拜望他时,他很高兴地送我一册留念,并一如既往地签名“一良谨赠”,先生对一切学人包括自己学生的谦恭令我十分感动和汗颜。 我和周一良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是陪同文化学者史仲文到周先生家里送书。那是1994年夏季的一天,当史仲文先生作为总主编的百卷本《中国全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因我与先生的相知,仲文先生遂请我介绍,一起到一良先生家登门拜访。先生是这套丛书的名誉顾问,出版社要把一套书送给他过目。事前我在电话里与先生约定了会见的日子,届时开车到北大去看望,同时也先后拜望了学界泰斗季羡林先生和张岱年先生,并给他们分别送去了一套《中国全史》。那一天,一良先生在燕东园24号住所的楼下客厅见到我,显得十分高兴,特意要我和他一起合影留念。 先生驾鹤西去时,我也正在病中,未能前往送别,成为心中永远的痛。他本来身体很好,80多岁高龄还坚持自己骑自行车外出,结果不幸摔倒,此后患病偏瘫卧床不起,期间我虽曾数次在电话中问候,但完全没有料到先生会如此匆匆离世,终究未再登门拜望。
哲人远去,学界同哀,周一良先生的治学精神和做人品格,永远是后学者的楷模和值得珍惜的宝贵财富。 [华声四海网声明:作者授权独家首发,版权所有,转载须知会] 
季羡林(周一良好友)在北大校园(2002年) 相关文章: 季羡林 《悼念周一良》
——载于2001年11月8日 人民日报第12版副刊《心香一瓣》 [本网编者按: 整理几年来的剪报资料 忽见一篇难得的真情文章 季羡林老先生对几十年来的人和事冷静评点 应可让一些非议者语塞。] 最近两个月来,我接连接到老友逝世的噩耗,内心震动,悲从中来。但是最出我意料的最令我悲痛的还是一良兄的远行。
...... 一良小我两岁,在大学时至少应该同学二年的。但是,他当时在燕京读书,我则在清华,我们读的不是一个专业,即使相见,也不会有深交的。一直到1946年,我在去国十一年之后回到北平,在北大任教,他在当时的清华任教,此时我们所从事的研究已经有一部分相同了。因为我在德国读梵文,他在美国也学了梵文,既然有了共同语言,订交自是意中事。我曾在翠花胡同预设中发起一个类似读书会一类的组织,邀请一些研究领域相同或相近的青年学者定期聚会,互通信息,讨论一些大家都有兴趣的学术问题,参加者有一良、翁独健等人。开过几次会,大家都认为有所收获。从此以后,一良同我之间的了解加深了,友谊增强了,一直到现在,五十余年间并未减退。 一良出自名门世家,家学渊源,年幼时读书条件好到不能再好的程度。因此,他对中国古典文献,特别是史籍,都有很好的造诣。他曾赴日本和美国留学,熟练掌握英日两国语言,兼又天资聪颖,个人勤奋,最终成为一代学人,良有以也。 中年后他专治魏晋南北朝史,旁及敦煌文献、佛教研究,多所创获,蔚成大师,海内无出其右者。至于他的学术风格,我可以引汤用彤先生的两句话。有一天,汤先生对我说:“周一良的文章,有点像陈寅恪先生。”可见汤先生对他评价之高。在那一段非常时期,他曾同人合编过一部《世界通史》。这恐怕是一部“应制”之作,并非他之所长。但是,统观全书,并不落他人窠臼,也可见他的史学功底之深厚。可惜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留下的几部专著,决不能说是已尽其所长。我只能引用唐人诗句“长使英雄泪满襟”了。 一良虽然自称“毕竟一书生” ,但是据我看,即使他是一个书生,他是一个有骨气有正义感的书生,决不是山东土话所称的“孬种”。在十年浩劫中,他跳出来反对北大那一位倒行逆施、炙手可热的“老佛爷”。当时北大大权全掌握在“老佛爷”手中,一良的命运可想而知。他同我一样,一跳就跳进了牛棚,我们成了“棚友”。我们住在棚中时,新北大公社的广播经常鬼哭狼嚎地喊出了周一良、侯仁之、季羡林的名字,连成了一串仿佛我们是三位一体似的。有一次,忘记了是批斗什么人,我们三个都是陪斗。我们被赶进了原大饭厅台下的一间小屋里,像达摩老祖一样,向壁而立。我忽然听见几声巴掌打脸或脊梁的声音,是从周一良和侯仁之之身上传过来的。我肃穆恭候,然而巴掌却没有打过来,我顿时颇有“失望”之感。忽听台上一声狮子吼:“把侯仁之、周一良、季羡林押上来!”我们就被两个壮汉反剪双臂押上台去,口号震天动地。这种阵势我已经经受了多次,已经驾轻就熟,毫不心慌意乱,熟练地自己弯腰低头,坐上了喷气式。 至于那些野狗狂叫般的发言,我却充耳不闻了。这一段十分残酷然而却又十分光荣的回忆,拉近了我和侯仁之和周一良的关系。 一良是十分爱国的。当年他在美国读书时,曾同另一位也是学历史的中国学者共同受到了胡适之先生的器重。据知情人说,在胡先生心目中,一良的地位超过那一位学者。如果他选择移民的道路,做一个终身教授,搞一个名利双收,真如探囊取物,唾手可得。然而他却选择了回国的道路,至今已五十余年头。在这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中,他走过的道路,有时顺顺利利,满地繁花似锦,有时又坎坎坷坷,宛如黑云压城。当他暂时飞黄腾达时,他并不骄矜;当他暂时堕入泥潭时,他也并不哀叹。......在这一点上,我虽愚钝,也愿意成为他的“同志”。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始终维持着可喜的友谊。见面时,握手一谈,双方都感到极大的快慰。然而,一转瞬间,这一切都顿时成了过去。“当时只道是寻常”,我在心里不仅又默诵起这一句我非常喜爱的词。回首前尘,已如海上蓬莱三山,可望而不可即了。
我已经年逾九旬,我在任何方面都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包括年龄在内,能活到这样高的年龄,极出我意料和计划。世人都认为长寿是福,我也不敢否认,但是看到比自己年轻的老友一个个先我离去,他们成了被哀悼者,我却成了哀悼者。被哀悼者对哀悼这种事情大概是不知不觉的。我这哀悼者却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七情六欲、件件不缺。而我又偏偏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我内心的悲哀实在不足为外人道也。鲁迅笔下那一个小女孩看到的开满了野百合花的地方,是人人都必须到的。问题只在先后。按中国序齿的办法,我在北大教授中虽然还没有达到前三甲的水平,但早已排到了前列。到那个地方去,我是持有优待证的。那个地方早已洒扫庭除,等待我的光临了。我已下定决心,决不抢先使用优待证。但是这种事情能有我自己来决定吗?我想什么都是没有用的,我索性不再去想它,停闭凝望窗外,不久前还是绿盖擎天的荷塘,现在已经是一片惨黄。我想套用英国诗人雪莱的两句诗:如果秋天来了,冬天还会远吗?闭目凝思,若有所悟。(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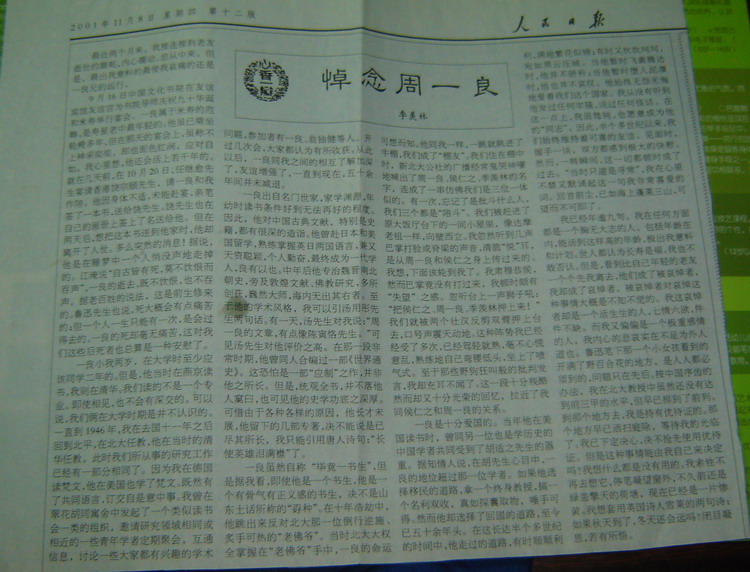
|